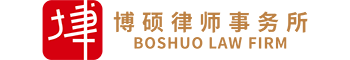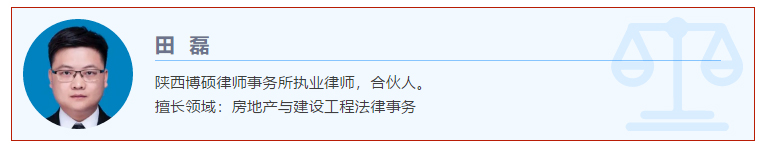
近期,笔者办理的几起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均遇到了这样的争议问题——发包人与承包人就工程结算、欠款支付等事项,在工程完工后签订的补充协议,是否属于双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从合同,其效力应否受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影响。实践中,很多人往往想当然的将后签署的“补充协议”认定为从合同。故特撰小文,以正视听。
【案情简介】 [案例一]:房产公司将位于西安太华北路某施工项目发包给建设公司施工,双方签订《施工合同》。2013年5月15日,房产公司与建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载明该工程已全部完工,并约定建设公司交房时间是2013年5月14日至16日;双方确认总工程造价为51233560元,欠付工程款为6623382元;房产公司承诺于2015年9月30日前付清全部工程欠款,否则,房产公司同意按实际欠款按每月1.5%的标准向建设公司计付违约金,直至款项全部结清止。 后房产公司并未全部付清工程欠款,我们接受建设公司委托,将房产公司诉至西安市中院请求: 判令房产公司向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5125677元以及按每月1.5%标准计算至实际偿还工程款之日的违约金。 房产公司辩称:该工程属于必须招投标的工程范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三项关于“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的规定。该工程属于施工合同单项(估)结算在200万元以上,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故《施工合同》当属无效。《补充协议》应属《施工合同》的从合同,亦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则不存在违约金的问题。故请求驳回建设公司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案例二]:技术公司拟就其名下位于西安市高新区的一宗工业用地进行开发。2014年10月29日,技术公司与建设公司签订《总包合同》,约定由建设公司承建技术公司开发的“某国际广场”项目工程。2014年11月7日,建设公司按上述《总包合同》约定向技术公司支付3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因工程一直未能开工,双方于2016年12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同意解除总包合同;保温技术公司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前退还建设公司3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如技术公司未按约付款,则应按照月息2%的标准向建设公司支付自2014年11月7日至实际给付履约保证金之日的资金占用利息。 后技术公司未按《补充协议》之约定付款。我们接受建设公司委托,将技术公司诉至陕西高院请求:判令技术公司向建设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3000万元及以该款项为基数按照月息2%的标准,自2014年11月7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 技术公司辩称:《总包合同》未经招投标,且双方均明知该工程所依附之土地为工业用地,故该《总承包施工合同》无效。《补充协议》属于《总承包施工合同》的从合同,亦属无效。其中,月息2%的利息标准,系基于违约责任约定的损失计算方法。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该约定当然无效。其主张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承担利息。 【我方观点】 上述两案中,我们均提出:《补充协议》系就双方既有债权债务进行清理的合同,其性质不属于施工合同的从合同,而属于独立的合同。故补充协议有效,违约责任、利息标准的约定当然有效。 【裁判观点】 陕西省高院在案例一的二审终审判决中认为:案涉工程为必须招投标的工程,双方所签施工合同未依法招投标为无效合同。房产公司主张双方《补充协议》属于施工合同的从合同,也为无效合同。但根据其约定,补充协议本身的目的和内容是确认房产公司欠付工程款的数额、支付期限、逾期不付的违约责任,因此补充协议在性质上属于对双方之间既存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和清理,具有法律效力上的独立性和约束力,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房产公司称补充协议为无效合同,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陕西省高院在案例二的一审判决中认为:涉案工程至今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双方所签《总包合同》未经招投标为无效合同。本案总包合同未实际履行,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技术公司向建设公司返还履约保证金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是一独立民事法律行为,不应受双方签订的总包合同效力的影响。《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注:本案保温技术公司上诉至最高院,二审开庭后其撤回上诉,故该一审判决为生效判决。) 【基于新规的说明】 实际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 于2018年6月1日起施行后,2000年5月1日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布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即已废止。2018年6月6日,《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规〔2018〕843号] 施行后“商品住宅,包括经济适用住房”不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范围。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上述两案中的项目均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划审批手续,据此判断两施工总承包合同俱为无效合同。当然,司法解释二施行前,两案判决皆已生效,不应再多评述。但陕西高院在案例二的一审判决中,以案涉工程未取得建设工程未取得规划许可作为判断施工合同无效的理由之一。笔者个人认为,应予点赞。 【案例扩展】 司法实践中,合同当事人在签署一份合同之后,再签署诸如补充协议、结算协议、付款协议以及承诺书、保证书等文书的现象,不乏其例。而包括很多法律从业人士在内的人员,往往想当然的将此后签订的文书,认定为首份文书的从合同,认为首份合同无效,其后签订的文书皆无效,这是很不恰当的。 一、从实践的角度出发,为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提出如下观点: 1、完整的一个交易过程,与一个法律关系,截然不同 日常生活中,一次交易过程,往往只包含一个法律关系。如,一单货物买卖,包含一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一笔金钱借贷,包含一个借款合同法律关系。然而,在复杂的市场经济中,一个完整的交易过程,更多充斥着多种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如,一个项目施工过程中,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除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外,还可能存在借款合同、让与担保等法律关系。再如本公众号此前发布的《以案例说起:一场重特大火灾引发的连环案,看律师如何诉讼,定分止争》一文中,就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与侵权法律关系竞合的复杂情况。实践中,很多人潜意识里将一个交易过程等同于一个法律关系,进而导致其认为后签合同为从合同。 2、同类法律关系,与同一法律关系,也不相同 如上所述,此种现象也是日常生活、市场经济中的常见误解。比如,电缆公司向建设公司施工项目供应电缆,与其就项目中的数栋建筑物,分别签订电缆供应合同。此种情形下,电缆公司与建设公司存在的是数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非同一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诉讼中,因该数个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可作为一案诉讼,这就更导致此种误解的发生。殊不知,数个买卖合同关系可一案诉讼,乃是基于共同诉讼的原理。 3、一份合同,并不必然只包括一个法律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须知交易主体订立合同,是基于其现实利益问题的需要而安排合同内容的。因此,也存在着就共同主体间的诸如借贷、买卖、易货、服务,等等事项,全部约定在一份合同中的现象。此时,需对其中包含的具体法律关系具体进行分析。 4、将合同名称直接等同于合同性质,是极不妥当的 实际办案中,经常会出现名为某种协议,实际确是他种法律关系或意思表示的协议。如名为转让合同,实为代物清偿的协议(推荐阅读:本公众号此前发布的《从“做了算”到“说了算”,以物抵债您了解吗?》);又如名为买卖合同,实为让与担保的协议。 确定合同性质,应自确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始。而确定意思表示,应遵从《民法总则》第142条、《合同法》第125条规定的解释方法来判断(实际上,对于多个合同间的解释规则,上述法律规定也仅可作为参照)。望文生义的解释方法,是极不妥当的。 二、司法实践中对本文争议问题的裁判观点是较为统一的,推荐参考案例有: 1、薛理杰、陈强与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市交通运运输局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2014)民一终字第88号]; 2、普定县鑫臻酒店有限公司与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普定县鑫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2016)最高法民终106号]。 3、笔者办理的上述两案裁判文书分别为:(2018)陕民终19号《民事判决书》;(2018)陕民初92号《民事判决书》。(讲道理,该两案办理中,上述最高院判决即为笔者所援引) 三、在办理上述两案过程中,清华大学崔建远教授于核心期刊法学研究上发表的《先签合同与后续合同的关系及解释》一文,对包含本文争议在内的“合同联立”问题,进行了深入且极具创新性的解读。本文写作亦受该文启发颇深,“墙裂”推荐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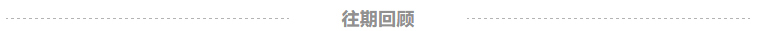
-
2020
04-01
-
2020
03-24
-
2020
03-16